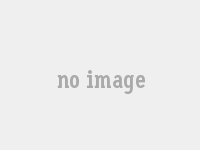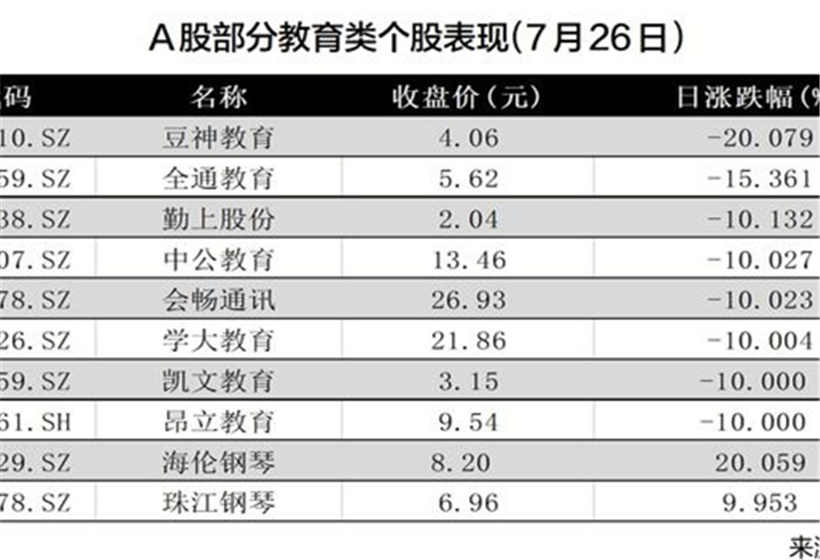茫茫人海中,您是哪一位?或许,您是热爱教育、爱好思考、研究教育问题,喜欢“琢磨”的人。或许,您是以教育为职业,为了做好工作,必须研究教育的人。或许,您是以教育研究为职业,为了做好工作,必须发表高质量研究性、思考型文章的人。或许,您是希望扩大研究成果传播度的人……无论如何,“思者”“痴者”“爱者”“乐者”……您是其中很重要的那一位。新的一年,我们将以更宽的视野研究教育,聚集思想前沿、教育科学、学校科研、域外教育研究等,期待您赐稿、评说。——编者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诗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着眼于流变的,认为变化是宇宙的本质。依照西方人的科学思维则是,变化是表面现象,不变才是宇宙的真谛。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是脱节的。高等教育秉承的是西方传统,而且面临十分紧迫的培养人才的压力,所以比较容易向西方学习。而基础教育更像中国的传统教育。
中国的家长还“不成熟”,如果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孩子能否考得上所谓名牌大学无所谓,也可以过幸福生活,社会对教育的期许肯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中国人的科技发展水平还暂时赶不上西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哪些方面妨碍了科学研究的进步?科学教育怎样弥补这些缺憾?近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他说,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可以弥补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先天不足”,但也妨碍了科学在更高意义上的发展。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了科学研究
记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科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科学研究、创新思维有何意义?
吴国盛: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诗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着眼于流变的,认为变化是宇宙的本质。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人生应该怎样渡过?人如何立于天地之间?中国人选择的是“顺势而为”。
依照西方人的科学思维则是,变化是表面现象,不变才是宇宙的真谛,不变性是世界的基本特点。科学的基本目标是要透过变化的表象去看背后不变的本质,这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的基本品质。希腊人发展出一种非常突出的对不变性的追求,比如,哲学研究存在,数学进行推理证明,逻辑学推崇同一律。希腊文化及后面的西方文化、现代科学,基本上也在沿袭这个思路。而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严密性、确定性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当然,这种欠缺并没有影响我们学习西方科学。从晚清时李善兰学习微积分以及后来的像钱学森、邓稼先等中国留学生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进行科学研究方面,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中国人这种普遍存在的诗性文化,并没有从根本意义上妨碍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和理解,没有妨碍我们培养出进行科学研究的“顶尖的头脑”。那么,中国文化学习西方科学的限度在哪里?统计上讲,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并没有拿到1/4的诺贝尔科学奖,连1/40也没拿到。这是一个标志。诗性文化所形成的风气,人群中的倾向性和氛围,妨碍了人们对科学的学习和对顶尖科学的追求,影响了教育,影响了科技人才的培养。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务实性。中国人往往务实而又灵活,不拘泥于一些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见机行事,与时俱进,等等,这是很重要的东方智慧。这样的智慧在什么时候有用呢?比如,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能够土法上马、因地制宜。比如,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奇迹。但是这不能说明你能够“领头”,发挥引领作用。现代化、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等,是西方首先提出的,其标准是西方创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在现代是有生命力的,但这个生命力还没到可以创立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的程度。
记者: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吴国盛: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个是说,这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自身有其生存智慧。比方说,儒家对科学并没什么大兴趣,但儒家并没有妨碍科学发展。整个中国近代史,儒家思想扮演了很正面的角色。它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为了报效祖国“硬着头皮”学科学。就是说,有些年轻人并不喜欢科学,但是他知道科学是今天富国强民的唯一道路,怎么办?他们的选择是,“我们一定要学”。钱伟长进清华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但是他觉得中文系不能够救国,所以就改学物理学,进行工程研究。中国人的这种家国情怀,鼓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报效祖国,硬着头皮去学西方科学。
这个跟西方纯正的科学研究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认为,学科学是因为喜欢科学,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发现宇宙的奥秘、发现真理、发现科学规律。这就是说,在促进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科学事业发展上,儒家有正面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学以致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文化,妨碍了科学在更高意义上的发展。科学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一种纯粹的真理性追求。如果缺失了这个维度的话,难以搞出那种纯粹的、具有引领性的、基本的学问。
当前的科学教育怎样应对挑战
记者:您认为当前的科学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吴国盛: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目前面临一定的困境。这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有密切联系。第一,中国的传统教育是精英教育,古代人大部分文盲,读书就意味着创造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第二,中国的知识遗产是以“经”的方式存在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策略主要是死记硬背,把圣贤书背熟了,然后慢慢体会它的意思。这里面有些是有道理的,比方说语言文学部分,从小熟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会优化和提升你的语言,从而内化到你的心理,使你的心灵变得很美好、很高雅。但是对于那些思想性、历史性比较强的内容,如果只能背诵却不能理解,除非反复背诵,否则就忘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及教育特点,使一些记忆力很好的人成为文化精英。这种死记硬背、大量做题的教育方法,应试起来有用,但培养不了创造性的人才。
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是脱节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秉承的是西方传统,而且面临十分紧迫的培养人才的压力,所以比较容易向西方学习。而基础教育更像中国的传统教育,授课内容、师资水平和培养方式以及整个中学教育的目标,沿袭了中国传统模式,这种死记硬背、条条框框、标准答案等,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过去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今天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学习方式却是传统学习方式,所以就会引发一种悖论。这才是今天我们的科学教育遇到的最大问题。
现代科学教育是源自西方的,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几乎是“无缝”接轨,大学里采用的教学方案和方法,在小学里就开始使用了,小学生就开始动手做实验,自己写论文,到图书馆查资料,在课堂上与老师进行讨论,等等。可是我们,直到大学甚至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如此培养学生。
记者:有什么改革契机?
吴国盛:真正的科学教育,要培养学生对世界的兴趣、自然的兴趣,对真理的爱好。现在的改革契机有两个。
第一是弱化高考“独木桥”效应,高校形成独立的招生考试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出路”,给孩子多次选择机会。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解决。一个是把好资源、好老师集中在几个学校里,冲刺世界先进水平,形成学生人生的独木桥效应。这个思路必然导致上行下效,大学分级、中学分级、小学分级,结果是形成了生源筛选机制,强化了应试教育。这不是一个国家应该采用的策略,国家策略应该是极大地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美国是公立和私立教育并存,而且都有名校。对美国学生来讲,有人认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有人认为耶鲁大学第一,有人认为芝加哥大学第一,有人认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被他们认为第一的学校,可以列出三四十个。在义务教育阶段,美国会强制性地让教师流动起来,这样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名校”。
二是过去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被边缘化了,专业学校改名为大学,中专改为大专,大专改为大本,大本升为研究性大学,高中生似乎只有考大本才是唯一出路。在德国,大学并不是所有高中生的唯一选择,在技工学校学习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一些传统产业有自己的技工学校,比如奔驰汽车公司、莱卡相机等,都是很令人羡慕的。
第二是吸取西方先进的中小学教学理念。借鉴西方启发式教育方法,“做中学”。近年来中国的科技馆免费开放,使孩子有了新的眼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很多实验室也建立起来了。优质中学也开始鼓励学生到国外学习,引进西方的科学教育教材、教案,不断在改善科学教育。
记者:家长在改进科学教育方面起什么作用?
吴国盛:家长当然是有责任的,中国的家长还“不成熟”,家长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三观),影响到对教育的选择。如果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孩子是否考得上所谓名牌大学无所谓,也可以过幸福生活,社会对教育的期许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以前的家长和目前这一代家长还不是这样想的。等到人们丰衣足食以后,慢慢地对一些虚幻的目标开始降温、淡化,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许会好一点,更利于教育的良性发展。
记者: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起哪些弥补作用?
吴国盛: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实施起来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第一个原因是整个大学架构是专业教育。教师有他自己在某个院系和专业的“生态”位置,而现实是,拿物理专业来说,研究表明,90%的物理系毕业生毕业后不从事与物理相关的职业。那就意味着,对多数物理系学生来说,还应该更多地去学一些人文的、社会的内容,以应对将来的职业生涯。而对于将来从事物理事业的人来说,这些人文的、社会的内容,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原因是通识教育的教师要懂得怎么教这帮孩子以一种通识的眼光去学习。比如,圣约翰大学是很典型的采用通识教育的大学,不分专业,教师在课上带着学生读历史上的各种经典,并进行讨论。学生如果要做专业研究,大学毕业以后再去攻读研究生学位。像美国的很多专业是没有本科生的,比方说最热门的三大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因为专业学院不是培养“人”的,而是培养“才”的。
科学教育怎样呵护科学精神
记者:科学精神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
吴国盛:中国人的科学概念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价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把科技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
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记者:科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吴国盛:科学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每个人有机会去释放潜能,人具有很多潜能和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和潜能就使得教育成为可能,也使得教育结果呈现出多样性。教育实际上自身存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教育有一个目标导向,可另一方面,教育恰恰是要呵护人类那种不确定性和它的那种自由的空间,保护人类天生的创造性。教育实践就是要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教育就是在这种平衡之中前进的。
记者:博物学如何助益科学教育?
吴国盛:博物学是西方的另类科学传统,整个西方博物学(自然志)都是如下两个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个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一个是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的传统。关注博物学传统对于理解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的发展主线是必要的补充,对于应对现代性的危机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如此,把博物学视作一种合法的科学传统,有助于以宽阔的视野容纳非西方文明,为非西方文明之中的“科学”正名。通过博物学,我们可以扩展科学的含义,打造广义的“科学”指称,重建科学谱系。
《中国教育报》2018年01月04日第6版 版名:理论周刊·思想前沿